
具茨山下,溱洧河畔。黃帝故里,鄭韓故城。在人類文明初露曙光之際,中原大地的先民們,就開始用他們雙手和智慧,書寫起輝煌燦爛的河南歷史。
行走河南,集零光片羽織就中原文化之錦緞。5月16日,由鄭州報業集團旗下正觀新聞·鄭州晚報主辦,一汽-大眾、星聯城、郵儲銀行鄭州市分行、浦發銀行鄭州分行特別支持的2023“行走河南”黃河文化探訪之旅采訪團隊,從位于鄭州CCD常西湖的星聯城出發,來到此行第一站——新鄭,走進鄭國車馬坑遺址、裴李崗遺址和歐陽修陵園紀念館,重新梳理新鄭作為“尋根之地”的文化淵源。?
在鄭國車馬坑
見證東周的時代變革
九州腹地,天地之中;北偎黃河岸,西托具茨山。新鄭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最早發源地之一,但很少有人知道,新鄭這個名字同樣有著悠久的歷史。
《詩經·鄭風》有詩曰:“溱與洧,方渙渙兮。溱與洧,瀏其清矣。”早在公元前769年,鄭桓公遷都于溱洧之水交匯處,定名新鄭,自此這座城市的名字就再未變更過。
鄭莊公以其雄才偉略,帶領鄭國迅速崛起,開啟了群雄爭霸的變革時代。從春秋時期的鄭國到戰國時期的韓國,新鄭有500多年的國都史,被后人稱為“鄭韓故城”。

這段消逝在時光中的恢弘歷史,讓新鄭在史書中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,也給這片土地留下了“露天博物館”的美稱。而鄭國車馬坑遺址,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,也是最讓人震撼的遺存之一。
“鄭韓故城平面呈牛角狀,俗稱‘四十五里牛角城’。車馬坑遺址在后端灣一帶,三面環水,是一個難得的風水寶地,因此有二十多位國君葬在地處。”據鄭國車馬坑博物館馬嬌介紹,該區域有春秋墓3000余座,大中型車馬坑23座,其中6米以上的大型墓近180座,長寬均超過20米的特大型墓4座。其貴族墓與車馬坑數量之多、規模之大,是東周文化的奇跡。
在鄭國車馬坑博物館內張貼的墓葬地圖上,密密麻麻標記著大大小小的墓穴之所在。其中,鄭公“中”字型大墓是目前全國發現的第一座春秋時期帶墓道的大墓。該墓總長45米,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南北墓道上大量的實用葬車,以及形式巨大的三棺兩槨,顯示了鄭國國君的顯赫地位。
據馬嬌介紹,春秋時期,戰事頻繁,車輛是名副其實的“第一商品”,車馬的數量也是衡量諸侯國軍事實力重要標準。

“如果把它的陪葬坑3號與2號車馬坑內的葬車數量加在一起,其車輛總數可能超過百輛,這對于當時號稱‘千乘之國’的鄭國來說,也是豪華陣容。反映的是這位國君已經‘僭越’不服周禮的客觀現象。”馬嬌如是說。
正因如此,鄭國車馬坑遺址映照著孔子口中“禮崩樂壞”的社會面貌,見證了春秋時期諸侯爭霸的時代變革。
由于保護困難,鄭國車馬坑已挖掘的部分,只占據了整片墓葬區的冰山一角。鄭國車馬坑博物館原館長李宏昌感慨說:“鄭國車馬坑的規模很大,它構成了我國截止目前春秋時期葬車最多、規模最大的地下車馬軍陣,比聞名中外的秦陵兵馬俑軍陣還要早四百多年。”他頗為遺憾地表示,最初發掘時,車馬上留有紅色的顏料,表現出鄭國“尚紅”的社會風尚,但出土后很快就消失不見了。
經歷兩千余年的歲月侵蝕,由木頭制成的葬車已與泥土凝固在一起,形成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木和土的結合體。唯有在一輛儀仗車下發現的象牙車踵,仍保留著曾經的模樣,向世人訴說著2700多年前的新鄭往事。
在裴李崗遺址
尋找人類的逝去童年
作為新鄭的標志性河流,溱水與洧水在《詩經·鄭風》中頗有存在感,它們不止映照著先秦諸國的興衰起滅,還在更遙遠的過去,吸引著先民的駐足。
浩渺清澄的溱洧兩河,匯流而成雙洎河,在這片水域東北側河灣的一片崗地上,有一個名為裴李崗的村莊。初夏時節,沿著鄉間小路,探訪團隊駛過泛起層層綠波的麥田和掛滿了青杏的果樹,入目即是濃郁而純粹的田園風光。
然而,就是這片崗地出土的石磨盤和石磨棒,將人類文明的曙光推進到了8000年前,也讓“裴李崗”這個看上去平平無奇的名字,響徹了大江南北。
提起裴李崗遺址,不少人都能圍繞其發掘意義說上幾句。諸如“填補了我國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時代早期的一段歷史空白”“證明了早在8000年前我們的先民就已開始在中原定居”“展現了我國農耕文化的起源”云云,都是中肯的評價,也在事實上確定了它的考古學地位。
但在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、裴李崗遺址現場發掘負責人李永強看來,裴李崗遺址對公眾的價值,不在于這些宏大的、被高度概括了的意義,而在于那些具體而微的事物——古裴李崗人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樣的?他們和現代人有什么聯系?

“這里出土的壺、碗、鍋、鏟,以及用來過濾的器物,和我們現代人使用的區別并不大,起碼我們一看就知道它們的用途是什么。可以說,遠古人創造出來的東西,讓我們至今受益。”站在考古發掘現場,李永強介紹起裴李崗遺址的最新研究發現。
有趣的是,研究隊曾在兩件陪葬陶壺中,檢測出了豐富的紅曲霉菌絲和閉囊殼,以及具有發酵特征的稻米淀粉粒。他們據此推測,陶壺是用于釀酒和儲酒的,甚至古裴李崗人種植糧食的初衷,很可能就是出于對酒的需求。
李永強還談到,從前裴李崗遺址的年代一直被認為是新石器時期。但自2018年遺址發掘重新啟動以來,考古出土了26000年前的鴕鳥蛋串珠、細石器和牙齒,證明在舊石器時代晚期,裴李崗地區已有人類在此生產、生活。
“把蛋殼穿起來做成項鏈,可見當時的人已經有了愛美之心。我們還發現了疑似植物纖維染色的痕跡,這是一種藝術化的追求。”李永強認為,舊石器時代的晚期智人或許就是我們的直系祖先,因為“他們的生活方式、思考方式,以及對工具的設計思路,都和我們是差不多的”。
李永強將自己多年以來奔波于田野的考古工作,視為對“人類逝去童年”的尋找。在他的講述中,先民向中原地區開拓進取的關鍵步伐被一一還原,這塊孕育了古老生命與文明的土地也熠熠生輝。
在歐陽修陵園
感念醉翁的文脈傳承
俗話說,人杰地靈。新鄭作為人文始祖軒轅黃帝故里、中華民族和華夏文明的重要發源地,誕生了黃帝、子產、韓非、張良、白居易、高拱等數不勝數的歷史文化名人。但有這樣一個人,他生前與新鄭的交集不多,死后卻在這里留下了可稱為“傳說”的非物質文化遺產。
他,就是自號“醉翁”的一代文宗歐陽修。
新鄭市城西13公里處的歐陽寺村,是歐陽修的長眠之地。公元1075年,歐陽修被宋神宗賜葬此地,其后他的第三夫人薛氏和他的四個兒子、兩個孫子陸續葬入,逐漸形成了歐陽修的家族墓群。又因歐陽修墓前建有敕建寺院,該村就以“歐陽寺”為名。
歐陽修陵園紀念館講解員劉彪向探訪團隊介紹說,祖籍廬陵(今江西吉州永豐),生于綿州(今四川綿陽),長于隨州(今湖北隨縣)的歐陽修,之所以會葬在新鄭,主要與宋代的一項喪葬制度有關。他表示,“三品以上的大臣要賜葬在京畿500里以內,而且北宋的皇陵在今天的河南鞏義,當時的文人士大夫,就已能夠陪葬在皇陵左右為一種無上的榮耀。”

據《新鄭縣志》記載,古時的歐陽修陵園,碑碣林立,古柏參天,郁郁蔥蔥,遮天蔽日,每當出現煙霧升騰的景象,不出三天,就會下起綿綿細雨,如煙似雨,景色非常壯觀,故有“歐墳煙雨”之美稱。
歐陽修曾有言“生而為英,死而為靈”。一代文宗歐陽修,不僅在當時有崇高的威望,是當之無愧的文壇領袖,而且對后世也產生過深刻的影響,在中國文學史上和學術領域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。他所創作的《朋黨論》《新五代史·伶官傳序》《醉翁亭記》《秋聲賦》等作品,寄寓了寬簡有度的政治理想和寄情山水的人生感望,一直是廣為傳誦的佳作。
故而在數百年間,無數名人志士前來吊祭、拜謁歐陽修。可惜在近代歷次政治運動中,歐陽修陵園慘遭破壞,垣墻倒塌,碑碣流失,900株古柏盡毀,僅存一株。
1994年,在政府和有關人士資助下,新鄭市重新修葺了歐陽修陵園紀念館。大殿塑有歐陽修坐像,以供祭祀;中殿內矗立有明代的“宋太師歐陽文忠公之墓”石碑;東配殿則是蘇軾手書的歐陽修著名代表作《醉翁亭記》碑刻展;祭殿后便是歐陽修墓,并排右側是其繼配夫人薛氏墓。
館內還移植了數量眾多的青松古柏與翠竹花草,樹影婆娑,光影斑駁,那個寫出“醉翁之意不在酒,在乎山水之間也”的人,終于能夠再次安眠于山水之間。
行走其中,草木掩映著琉璃碧瓦,恍然間,人的心靈似乎也能穿梭千年,與先賢隔空對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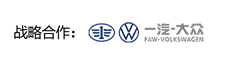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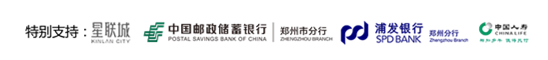
正觀新聞·鄭州晚報記者 張曉璐/文 徐宗福/圖?
采訪團隊:舒晗 樊無敵 陳君平 張俊 楊雅晴 鄭治紅
